关于教会史,常读常新的四南京白事服务网4000253450本“大家小书”
笔者常读常新的一些学术专著,南京白事服务网4000253450有的是多卷本,厚达上千页,有的篇幅较小,不过百页左右,而几十页的小册子也所在多有。当然,篇幅大小并不是衡量书籍价值的标准。不过就阅读体验而言,倒是一些“大家小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专业所限,所谈的几本书泰半围绕教会史这一主题,可能稍显冷僻,但其中蕴含的思路和方法论却不无启发之价值。
几年前我在爱丁堡大学进修,曾在终身教育学院选过一门“近代欧洲史导论”。在修习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其一是,这门课给予新教的权重过大,留给天主教的空间很小,基本上仍旧是新教彰显进步、天主教代表反动的所谓“冲击与反应”模式。其二是班上的一位同学多次表达她对宗教对抗乃至杀戮的困惑,这让我很感动也很震惊。她当时已经退休了,住在爱丁堡远郊。她说小时候亲见两个村子因为捍卫不同信仰而时常斗殴,发生流血事件。凡此种种,均给她带来很大的伤害,也成为她心中难以解开的一个结,所以她选择来学习历史。但有意思的是,在她多次表达对宗教对抗的愤恨,并屡次质疑老师讲解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既非天主教徒亦非新教徒的“他者”,反倒发现她身上有着浓厚的新教情结,也有着那种对天主教的化不开的轻蔑;她之寻求答案的精神让人钦佩,但她始终为自己的后设观点束缚而不自知,也着实让人感到遗憾。
课后,每当房东或合作导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会向他们提起课上遇到的情形,他们笑言苏格兰是非常世俗(secular)的社会,倒是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要“religious”得多。为何经历宗教改革的欧洲会加速世俗化的进程?这是当时的新教领袖所能设想的吗?这是始终认为自身毫无变化的天主教会所乐见的吗?为何美国要比英国的基督教信仰更浓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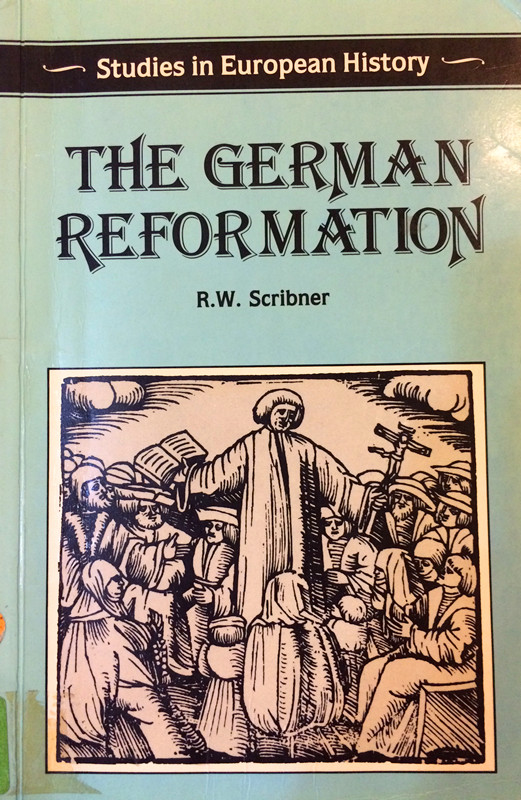
上世纪7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有两位年龄相仿的史学新星冉冉升起,其一是美国文艺复兴史专家埃里克•科克伦,另一位便是在英国讲授宗教改革史的澳大利亚人斯克里布纳。彼时两位已经推出重量级作品,并挑战旧说,在业界占有一席之地;学界咸信假以时日,他们必然成长为巨匠。但天妒英才,上世纪末,两位均在50多岁的盛期因病去世。特别是斯克里布纳,当时已转往哈佛任教,正要开启另一番天地。两位才子的遽然离世,让学林不胜唏嘘。
斯克里布纳是推动宗教改革研究“社会史转向”的先锋之一。概而言之,彼时的宗教改革研究为两大迷思所笼罩,一是辉格史学的目的论进路,亦即“现代化”假说:以宗教改革的成型与发展为结果和出发点,将马丁•路德视为现代第一人和现代自由之先驱,把历史的演进目为由落后向进步的必然进程。二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说”,强调加尔文主义在日常伦理中与资本主义发展之勾连,认为天主教、路德宗等并无这一“基因”。这两种观点都是非常“世俗化”的历史迷思。此外,还有新教历史书写传统中的“天启说”,亦即路德乃上帝所派之大卫,而天主教会是必亡的歌利亚。天主教不但被污名化,而且失去了历史书写的主体性;新教则成为另一块铁板,成为教科书书写中无需细辨的题目。
斯克里布纳在那本小书中用精到的语言论析了上述种种迷思的问题所在。而他因应的方法便是社会史进路,亦即宗教改革不是一个结果如此简单的事件,而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其间充满了反复与纠缠、对抗与博弈;除了主要改革者和世俗君侯的种种思想与作为,普通信众绝不是被动接受日常生活巨变的一方,实则他们对信仰之体认以及他们对宗教演变的反应不乏创造性,他们与“菁英”力量之间的互动、激荡更是宗教改革嬗变中的重要一环。若对此不加以考辨、详查,不仅难言厘清历史脉络、勾勒历史实相,反倒会建构更多的神话。
此外,在70年代,斯克里布纳还将文化理论、人类学相关理念与社会史加以整合,在本书中也有体现。譬如,韦伯之宗教改革的“袪魅说”以及背后的新教理性之观点,广为学界所熟悉,迄今还在我国为人所乐道。但斯克里布纳借由开掘大众信仰的具体表现,揭橥在特定时段内的新教的另一面,亦即它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保有的迷信的一面、非理性的方面。凡此种种,在当时都给宗教改革研究注入了活力,也大大动摇了既有的诠解框架。可以说,斯克里布纳这本小册子简约而不简单,篇幅虽小,学术性则相当重,是一本越读越厚,越读越让你发觉天地之大的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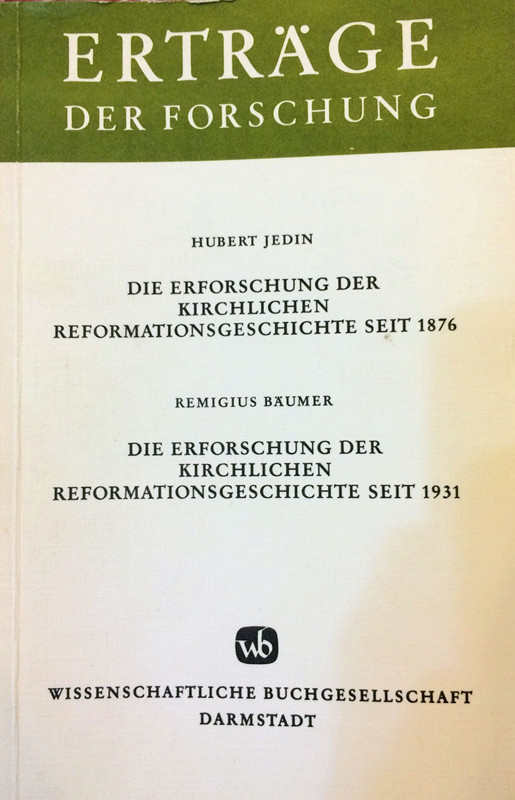
通过这本小书,我们一方面可以体会到天主教一方在撰写宗教改革史过程中所经历的彷徨、迷惘,也可看到教派性论争一度居于主流,而持平之作则在封闭且严酷的教会氛围中破土而出的诸番努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自二战以还,天主教史家对宗教改革的研究益趋细化,也日益自省,开始尝试对路德和加尔文的历史形象做出持正的描绘;抑有进者,还顺势发掘彼时天主教自身的历史,以求说明宗教改革时代天主教历史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如果将这本小书与斯克里布纳的那本小书加以对观,则大大有助于把握会宗教改革研究的核心议题。

另外,我还发现一位重要学者也对奥马利的这本书青睐有加。他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史名家康斯坦丁•法佐尔特。他指出,此书虽是由一位天主教耶稣会士所写,谈的也是天主教的历史,但其中蕴含的史学史现象、史观的演变以及各种方法论之间的竞技,不仅精彩至极,而且是了解如何撰写学说发展史的绝佳范例,不容错过。

所谓“异端”人士,到底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的神学观、世界观是如何形塑的?何以他们在那个宗教氛围浓烈的世界反倒与周遭之人如此不同?他们的思想与人文主义有何勾连?他们是19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先驱吗?抑或只是由自由派史家为满足自身关怀而建构的想象?这些问题,我并没有答案,但在阅读意大利历史学家马西莫•菲尔波的名作《16世纪意大利的新教改革和异端:一个历史面相》(Massimo Firpo, Riforma protestante ed eresie nell’Italia del Cinquecento: Un profilo storico, Roma: Editori Laterze, 1993)的过程中,渐而加深了对彼时历史的认识。
马西莫•菲尔波是治宗教史的意大利世俗史家的典型代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非教会背景的意大利学者,向来对罗马教会的制度史、结构史没有兴趣,他们秉承自由主义学说,接续的是克罗齐这类自由主义知识人的文脉,反感、厌恶教会的社会控制,故而对“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群及其历史兴趣浓厚。借由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在兰克笔端隐而不见的那群“异见分子”,也可以体会为何迄今意大利的教会背景的学者与世俗史家仍旧保持着对立紧张之关系,甚至还可以对当今意大利社会的宗教矛盾有所感悟。那种历史的撕裂在在是其来有自。
以上所谈的几本书,时而答疑解惑,时而提出新问,陶冶和形塑了笔者的学术口味与视界,算是个人学思历程的一个反映。拉杂写来,纯属“私人口味”,尚祈方家指教。